
孙青(章静绘)
距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过去了一百三十年,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依然引人瞩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青副教授最新出版了《知识的秩序与环流:甲午战争早期史叙的知识史考察》一书,将讨论的焦点从战争转投向战史,以甲午战争期间及战后近三十年内,以中、日、西文书写的早期战争史叙,追问近代国际战争、全球化等十九世纪中后期发生的全局性变动,如何搅动了旧有的知识秩序和知识空间,又缔结了何种新的图景?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她认为:“战争搅动了社会,从知识史的角度来讲,知识空间重组了,在重新缔结。原来的秩序,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秩序,文本的秩序,都发生了变化。”只要环顾我们当下的世界,对此就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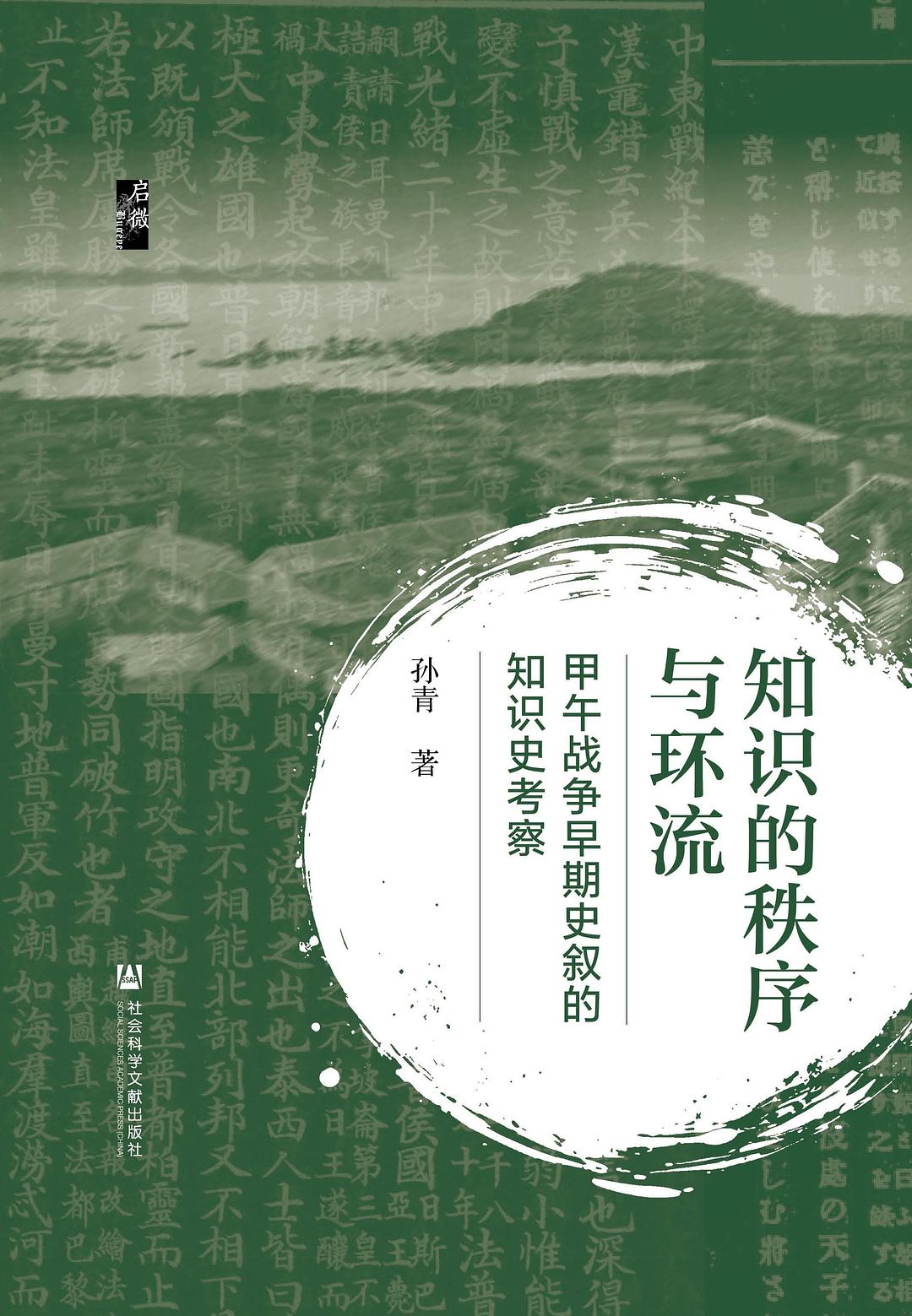
《知识的秩序与环流:甲午战争早期史叙的知识史考察》,孙青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版,356页,89.00元
全书的核心概念“史叙”指什么,与现在比较流行的“历史书写”这一概念有什么不同?
孙青:本书交替使用“历史叙述”“史叙”,用来指涉各种对战争的记述,这种记述基于经验见闻(而非逻辑推断或虚构想象)所作,强调历时性视角并追求某种“内在一致性”。其具体形式可以包括文本、图像及其他衍生文类。它们中的大部分在不同语言文化语境中,常会以“史”“纪”“本末”“颠末”“history”等确定的文类标识作自我界定,有些则不以固定的物理文本形式呈现,而是停留在流动中的片段叙述状态。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错谬的话,“历史书写”概念是近年来全球历史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概念,通常指对历史叙述的建构、呈现和阐释方式的反思。它不仅关注历史事实是什么,更关注历史是如何在特定叙述模式、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等外在限制下被呈现、阐释与传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书写”与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有很大关联,但又存在差异。
简而言之,目前学界落实到经验研究层面的“历史书写”讨论,大多较为重视从比对“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差异入手,讨论隐匿其后的叙述者的主观动因。而本书则更关注造成这类差异的客观因素,尤其是各类叙述机制诸如文类形式、书写格式、表达结构程式以及档案归集与馆阁书史制度等等本身的限制——书中称之为知识的“秩序”。也就是说,较侧重考察叙史制度与机制等隐性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变动对史叙文本的影响。
此外,历史叙述作为叙史活动对历史经验的各类非虚构表达,除了文字以外,也包括图像、照片甚至即时性的媒体报道。这些形式与基于逻辑推断或虚构想象的历史主题写作有所差别,也与强调盖棺定论时间隔断的事后追述性历史书写不完全一致。
从本书所处理的有关甲午战争的史叙来看,似乎这些具体的文献形式或明或暗采用“史”的标识,其着眼点有时更在于它的文类特征——如能提供某种全局性或整体化的阐释线索,将历史事实串联成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结构的经验过程等。比如1895年,日本人井上辻吉在东京出版的The Japan China War就是一个合订本。是在战争结束后,将他之前逐一分别单行的三种英文战史The Naval Battle of Haiyang、The Japan China War on the Regent’s Sword: Kingchow, Port Arthur, and Talienwan 、The Fall of Wei-hai-wei修订合并而成,汇诸役(battles)情形为一大战(war)之始末。也就是说,这些单行战史最初出版时,并不明确预知战役的发展方向与终点。初时,这些单行战史由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imited)在横滨、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的网点同时发行,声称主要依据了官方档案和一些别的材料,并采用了大量珂罗版照片,其用意是在强调自身非虚构的文类特征,而到了1895年合并修订本The Japan China War出版时,某种整体性的解释线索又被添加进去。
另外,目前学界有关历史书写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叙事性”是书写形式对经验对象进行结构化呈现及作出阐释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这种“叙事性”基本上是故事化的,主要工作是为历史过程建立事件发生的因果链环,并依据与事件因果发展的相关程度设置主从角色,以及陈述其行动与事件的关系等等,这种特征可以称为“事件化”。因此有一个相关联的分析概念就是“历史叙事”。不过,本书通过对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有关甲午战争的汉字、和文等官、私史叙形成过程进行经验观察,发现史叙的结构化方向还存在“事件化”以外的线索。我暂时尝试以“事务化”来勾勒追溯之。这种“事务化”的叙述方向,是以历史过程所牵涉的行政流程为主要线索和时空经纬来编织的。这一取向可能与汉字圈深远的文书行政技术、馆阁书史制度及从中央到地方的衙署文档归集机制密切相关。强大的官修书史传统与文书行政技术是东亚汉字圈较为突出的一个知识史的机制性特征,而十九世纪末恰是这个机制发生急剧变动的阶段。东亚汉字圈的精英原先依托汉字书面语、汉文史书传统、汉字典籍共同文本,以及源自典籍的公共议题等共识基础所缔结的知识空间正发生变动与崩解。而在这个变动中,史叙对历史经验过程的“事件化”与“事务化”这两个结构化取向将如何变化,是本书关注的重心之一。因此我采用“史叙”而不是学界较为习见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叙事”来加以锚定,背后的基本考虑大致如此。
按照您书中第一章的看法,传统的官方战争史叙与日常行政纠结在一起,这造成了什么特点与后果,而后来战史的撰写是如何从日常行政中“脱范”(或“脱嵌”)的?
孙青:严格来说,官方战争史叙大致包含了明清中央馆阁书史机制和各地官府主导下的方志书写等不同层级的官修史面向。官修史不仅仅在北京有,地方志实际上也是在官府主导下撰修的,体例往往也与中央机关撰修的志书保持一致。不过,书中所讲的官方战争史叙,没有完全覆盖所有的官史类型。因为本书讨论的对象是甲午战争的即时史叙,馆阁书史是其中最主要的官修史形式,方志尚未参与其中,因此我的讨论集中于这个层面。我后来在针对具体案例时,也较多采用“馆阁书史机制”的表述,以作限定。其实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阵亡将领碑传等内容,但它们与行政流程的纠葛较为间接。例如左宝贵的碑传,虽然在地方志中也有记载,但它是根据官方记述转述并加以补充的。这一部分的情况,应留待之后再做进一步讨论。
本书处理的几类清代主要馆阁书史类型,包括国史馆的“忠义传”、实录、起居注等等,其中最重要、最特殊的是军机处下设方略馆修的军事方略。这种专门讨论战争的、官修的军事活动专史,在中国历朝只有清代才有。为什么清代特别强调方略?这一问题恐怕还有待进行深入思考。有一个可能是跟雍正时期的西北用兵有关。方略所记战役,从清入关之前的“开国”诸战就开始了,它反映了清朝不断强调帝国武功的特点。我觉得这大概与清代的王朝合法性有关。因为清的合法性并没有过多借用明代的正统叙事,单一强调“奉天承运”型的权力来源,而是毫不讳言地持续强调王朝武功。
传统的官方战争史叙与日常行政纠结在一起,历史叙述服务于行政目的,造成的结果就是战史书写本身的事件因果链不很明确,呈现出明显的事务化特征。
在方略里,卷首的御制诗、御制文及告天表文完成的是对主题军事行动的事件化叙事。不过一旦到了正文部分,就是高度事务化了,主要是按照时序以摘录章奏、谕旨等公文原文来清理与呈现用兵本末,基本上就是档案的汇编。早期方略还会有“臣等谨案”领出一段编纂史官概括事件或歌颂帝王功德的文字,清中叶以后史官的主动措辞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
那么史官在哪些地方还能有所作为呢?我在写方略一节时做过梳理,比如可以改变档案之间的流程顺序加以辑录。我在关注《平定教匪纪略》时,发现了一种颇为珍贵的史料,就是方略馆在编这份纪略时留下的调阅辑录文献的全纪录《平定教匪纪略总档》,建立于嘉庆十九年正月初八日,终结于嘉庆二十一年五月。方略馆为编纂《平定教匪纪略》必须调取、挑选章奏谕旨,并逐日按文书责任人编目,侧重以事务化取向经纬史事。通过比对定稿发现,他们选了一部分总档的内容编进去,并且有些是改变了顺序抄录的。这是史官能做的事件化历史书写以外的事情。
国史馆修史的情况也相似。“忠义传包”中有很多草稿,都属于史官的日常功课。这些功课包括依据涉及恤忠立传行政流程的所有往来公文(通常为前线章奏、谕旨、兵部开具的传主履历单等)起草、增削、改定传稿。通过比对,我们发现“忠义传”撰修的一般原则是对谕旨“可节不可删”,即不改动谕旨确认过的表达。而对章奏所述阵亡事迹可以概括、归并,但也很少会增加溢出行政公文表述文字以外的史官主观叙述。所以,史书本身并不像我们今天认为的那样,仅仅承载着为王朝修史的政治功能,它实际上更是行政流程中事务性的东西。
国史馆的时候是这样,但到了帝制终结后的清史馆时代就不一样了,清史馆需要盖棺定论。他们自己对于编纂原则也说得很清楚,认为国史馆是“宁滥勿遗”,而自身则要考虑“千秋功罪”。当然,两者的传稿文本是一以贯之的,即清史馆继承了国史馆所有的传稿传包,甚至修纂人员也有不少父子相继的情况,只是编纂原则彻底变了。到了这个时候,历史修纂可以说已经“脱嵌”了。
私人撰史的传统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甲午战争的私人修史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官修还是私修,基本都围绕同一史源吗?相对于事务性的官史书写,我们更容易接触的是私人修史事件性、史论性的书写,它是否塑造了国人对甲午战争的常识性认识?
孙青:私人撰史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确实一直存在。但私修史的变化从明末就已出现了。明清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为什么明末私修史突然多了起来?因为《明实录》曾被烧毁过。之前《明实录》不允许大家抄,官方史料是不开放的。后来因为烧毁后开放了,所以就有不少士绅去抄官修史。这时就有大量私修史涌现,但这个私修史是基于官方史料的。清末也是这样,清末关于战争的很多私人修史,实际上有大量的官方史源,而且这个私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士绅。
我看到有学者的研究称之为“幕府修史”,我觉得这种说法还不太精确。因为很多人其实只是底层官员,并不隶属于任何人的幕府。也不是幕府非要修史。我整理了这些私人修史者的身份,包括他们接触到的材料来源。比如魏源编《圣武纪》,他当时担任什么职务能看到这些材料?有很多中低级司员,包括一些在兵部、通政司及各口洋关税司任职的人员,他们因为当时在从事相关工作,所以能接触到这些史料,然后自己回去就尝试叙史。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有关战争的许多私人撰史,有非常清晰的官方档案来源,撰写者往往服务于涉及战时文书流转的官署部衙,至少与之关系密切。虽然私修史的形式仍多使用前代就有的笔记体裁,尤其是“书事文”,但“私史官源”的特点很显著,并不能简单以“野史”目之。不能说,前代的私人撰史就一定没有类似的情况,但至少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私撰军事史中,是能够清晰地看到机制依据的。
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并不是仅仅发生在中国。比如朝鲜半岛的汉文战史,有一位作者李晚焘,他是春秋馆的史官。关于1894年6月21日发生的高丽王宫被围事件,他在春秋馆的日记中是一种写法,在私人的《响山日记》里又是另一种写法。后者细节更为丰富,更为血腥和混乱,包括高宗生父大院君出面谈判、终结乱局这些内容。而原来的《承政院日记》这种文本实际上没有为事件化史叙留下空间,因而无法去描述这些细节。当然他主观上的考虑暂时无法深究。很明显,就对“历史事件”的故事化曲折呈现而言,他更能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展开。不过,这类私修史同样也是“私史官源”的。
当然,由于清王朝官修史的开放程度有限,相关信息基本是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知识)共同体内流传。因此人们对历史的一般常识性认知很难直接从此获取,往往需要经过多次转手。本来内外军事活动就是明清私修史极为热衷的主题,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汉字圈各口岸城市的近代传播媒体又因战争报道而高度活跃。文字记载、图片、口说、游艺、教育考试等传播形式,都参与了战时及战后短期内的即时“叙史”,这一方面为私人修史提供了有别于此前的史源,另一方面也当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历史的常识认知。
您在书中对于史叙和史源有很多的讨论,而历史书写和史源学是现在历史学界比较热门的概念,您怎么看这种史学趋向?
孙青: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偏差,目前学界关注“历史书写”背后的史源问题,其实就隐含了某种知识秩序的判断。也就是说需要去推断哪种书写更“真实”,离历史经验最近。不过我的问题意识,重点并不在于依据史料阶序加以取舍,来线性证明某种更真的“真相”,而是对史叙的固有阶序加以对象化观察,并尝试突破单一阶序,将史叙还原到最初书写时所处的基础结构中去理解。虽然一定会用到史源学的方法,但问题意识却并不相同。简而言之,本书是知识史而不是史学史或讨论历史书写的著作,在追溯史源时,我更关心的是一个社会性的知识共同群体有没有一些最基础的共同文本(跨语言、跨区域被共同阅读、讨论和引述)的问题。基于我特殊的设问,很显然,仅靠判断谁更“源”、谁更“正”则无法解答,而需要别立视角。这一学术关怀在各章都有所体现,特别是第六章。
第六章讲《平定教匪纪略》,就是天理教这个事情(1813-1814年天理教教众在直、鲁、豫的军事活动)。我在讨论完全官修的《平定教匪纪略》时,通过将逐日原始章奏流水如《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编纂专档《平定教匪纪略总档》和最终刻板的《平定教匪纪略》加以比对;并对照同一事件的几种私修史叙,包括蒋湘南《七经楼文钞》中的书事文《书滑县平贼事》,盛大士撰《靖逆记》,魏源《圣武记》第十卷《嘉庆畿辅靖贼记》,昭槤《啸亭杂录》第六卷《滑县之捷》等,发现它们之间都有关联。也就是说当时即使是所谓私修史,其实主要信息甚至叙史的事件化经纬结构仍然是来自“官源”。
盛大士的《靖逆记》在序言中简短叙述了其书的编纂经过,提到他得以“恭读《钦定平定教匪纪略》”,证实了私史与官源存在勾连脉络。从日期来看,当时《平定教匪纪略》刚刚钦定、颁赐,仅有七十九位王公亲贵与部院督抚大臣可以看到,盛大士作为一个下层士人是怎么看到的呢?我有一些猜测,可能与书法家董诰(文华殿、入直军机,在颁赏名单之内)有关,董和盛在书画方面有交流。但无论如何,两个文本存在共同史源。
判断同一史源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例如直接引用皇帝的谕旨内容,行政文本,使用朝廷掌握且没有颁布的口供,以及一些保留了官方史源高度事件化痕迹的记载,等等。
那么官方史源是怎样流向私修史的呢?我接下来的研究要致力于把沟通官方行政文书与民间私修史叙的史源桥梁研究清楚。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史源所流通的人群,是否构成了某种特定的信息共同体?我猜测是有一个个小团体的,如十九世纪中叶的魏源、阮元、蒋湘南、盛大士等人,对天理教叛乱的叙史构成了他们的一个“公共议题”。这些圈子多以各部衙中下层官员为主,在日常工作中能看到官方档案。他们互相交流看到的文档信息,因此叙史的故事结构都很像。通过分析他们的身份、文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
所以我的问题意识一开始是很朴素的:消息是怎么流传下来的?私人修史者是怎么看到的?为什么叙事结构都差不多?最后它们凝结成这本书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关怀,就是哈贝马斯的“共同议题”。所谓共同议题,是指在某一特定时空中某些群体共同关心的议题,围绕这些议题的参与,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生成知识空间或社会性空间,因此这是人和人之间交往的一种特殊形态。这个议题一开始可能是诗画,后来战争爆发了变成战争,但是借着这个议题,讨论很可能已经溢出了这个战争的范畴。
比如翰林院编修丁立钧复命进呈《东藩事略》,以便及时满足光绪皇帝了解清朝和朝鲜关系的知识需求;同时附上《东事条陈》五条军政意见,讲对朝鲜应该如何用兵的意见。接下来他又给他的老师翁同龢写信,说自己写条陈的时候“大率人云,无甚深切之言”,只能写一些俗套的话,真正想要讲的话却“率非代奏可详尽”。他和翁同龢就说了他真正想讲的话,就是他对北洋派系把持政局的种种不满和意见。这表示关于朝鲜、中朝关系和这场战争是一个共同体的公共议题。他们都要从这件事说起。如果丁立钧不是因为编纂《东藩事略》,他在皇帝面前是不容易有发言权的;他和翁同龢之间的交流,也要从这场战争说起。
我认为,对于甲午战争的认识和历史叙述,已经是一个公共议题了。而且这个公共议题不仅是中国的,它是在整个东亚汉字圈的,甚至是跨越语言的公共议题。
这个公共议题有很多分支,比如文明决定论也是这个时候建立的。日本人认为文明决定论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从光绪皇帝或李鸿章的角度来说,文明决定论把一场战争的胜负关键与维新、西学联系起来,既然面对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战争失败就是必然的命运,不是他们的责任。光绪皇帝还把宣扬“文明教化论”的《中东战纪本末》刻好后送给朝鲜宫内厅的人带回去给朝鲜国王,可见他内心的态度。这套理论恰恰是日本也期待朝鲜接受的。但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意见,《东方兵事纪略》的作者姚锡光就提出,甲午战败的责任在于“封疆之吏”和“将帅无能”,没有必然导致战败的“世变”,一切都是“奇变”,是可以通过“明耻教战”来改变的。原来我们以为甲午战争中的文明决定论是举世都接受的,其实不然,其中还有隐藏线索,只是被后来的历史叙事湮没了。还有一点,文明决定论在那个时候的解释框架中可以平行移动,“文明”阶序不只存在于中西之间,也可以被平移到先完成“西化”的日本和清朝中国之间。
甲午战争期间,无论是清廷、日本军方还是民间社会,都出现了大量关于战况的谣言,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些战争谣言?它是知识生产必然带来的副作用吗?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清代的谣言,尤其是关于那些参战人员的谣言,原来就有一个体制上的容许空间,只不过在甲午战争时期我们看到它被更显著地呈现出来?
孙青:厘清“战争谣言”,虽然并不是本书主要关注的问题,但确实涉及了战时叙史的一些机制性(即前面提到的叙史“基础设施”)特征,值得展开说一下。
战争谣言产生有很多可能性,首先,是因为通信技术本身的问题。战争前线的真实情况没有人知道。就像甲午海战,两艘军舰都沉没了,丁汝昌最后说了什么话,是怎么传回来的?后来是通过获救的落水水兵询问口供才得知的。再比如作为战时掌控情报枢纽的盛宣怀,连自己的弟弟盛星怀在战争中的生死下落都不明确,他曾写过一封信让家里派姨娘来照顾受伤的弟弟,过两天又写信说弟弟已经死了,没有确切的消息。这是客观因素。其次,因为作战时朝廷随时进行恤功罚罪前线调查以激励战事,主观性的“讳败为胜”就常会发生。另外,战功奏报有自己的汇报要素,如杀敌人数可以作为阵亡将领所获祭葬及荫恤规格的依据。还有,为什么一定要写“洞胸一枪”,事实上记录者未必能看到这一枪,也未必有人真的去验尸,因为“洞胸”意味着正面迎击,“背后一枪”则可能是逃兵,一个是要奖的,一个是要杀的,后果大不一样。这些与历史过程脱节的叙述产生于行政奏报的流程中,本身是军政机制的一部分,但因为它们成了“忠义传”、实录等官修史最基础的叙述源头,往往被保留到最后,因此就成了叙史“谣言”。还有一个与谣言有关的机制在清代非常特殊,就是清代御史参奏“以风闻入奏”,甚至不需要情报的真实性,参奏事实上已经变成一种政治机制,一种统治权术。
总之,谣言呈现出非常多元的特点。牵涉政治机制、御史制度的变化等等,也有通讯技术的原因。现有研究从文化史角度解读历史上的谣与谶较为普遍,但实际上,却是政治管理实践的机制流程给谣言留下了可能性。
甲午战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较早有第三方国家媒体随军观战及参与报道的国际战争。西方很多国家的“战报”“战史”以及关于这场战争的“知识”,有什么样的特点?对于重新缔造东亚的知识空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孙青:我在书里讲到情报译写的问题。当时东亚参战三国主要的情报源很多是来自报纸。那个时候连总理衙门都是翻译《大阪每日新闻》《清日新闻》,《泰晤士报》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受命翻译情报最主要的来源。我们的情报线索基本以天津为枢纽,分为两条:一是各驻外公使,二是海关税务司(包括朝鲜仁川税务司)收集情报。海关税务司的情报来源主要是报纸,各地的驻外公使每日译报,或者把报纸递给总理衙门翻译。这就涉及情报来源的问题。那些西方报纸的记者都是拿着日本许可证的战地记者。情报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随军记者的写作,二是他们的报纸,三是相互之间的翻译。其实《泰晤士报》也会翻译我们的中文资料,这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环流”。其实连画报图片都是环流的。我们的宣战谕旨第二天就在《泰晤士报》刊登了,《申报》比《泰晤士报》还晚,这种报刊上的报道,在今天看来只是民间的信息流通,但在当时却是军事信息的重要来源。
甲午战争期间及战后短期内的媒体报道,也影响了近代东亚的知识空间。
过去我们说的“汉字文化圈”,是西嶋定生提出的,我们总是在说日本人是如何学习我们的汉字。金文京有一本书《汉文与东亚世界》,他想要表达的是,当汉字成为这个区域精英共同书面语工具之后(我们常说日本、朝鲜、越南用汉字,其实是那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共同政治文化生活中使用汉字书面语,而不是全民现象。也就是说,汉字文化圈其实是个精英文化圈,它是有阶层性的书面语传统),它就开始自我繁殖了,就像人工智能一样,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汉文世界”。陈力卫老师的研究就提到,日本的汉字书面语在江户时代以后,开始吸取明清小说的文本来更新汉语书面语修辞,逐渐注重有活力的汉语口说传统,而不仅仅局限于依据精英经典文本。这时汉语书面语已经从极少数精英往下走了一点,向参与共同政治生活及文化传播的一般经史读写群体延伸。而到了甲午战争这个时段,日本恰恰因为对战争的新闻报道,而使得汉字书面语的修辞、体裁、内容及目标读写群体的变动变得更加剧烈。
原来日本的报纸是非常精英化的,大报全是汉字,连假名注音都没有,而且都是论述式的,精英坐在家里就能评论战争。甲午战争时期,开始出现商业化报道,有不少新闻记者奔赴前线。老百姓想要看实时报道,但这种报道一开始对他们很有难度,因为汉字太多。一开始,对于老百姓来说,要通过每天分散的实时报道来理解事情的全部颇为困难,他们没有那种通过主动思维来逐步整合事件全貌的阅读习惯。大报以前多采用精英灌输模式,直接以汉字书面语给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和评价。而底层小报虽不采用这种形式,但人们接受故事,多需要配图才能理解,就像连环画一样。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分化,就是如何通过图片和片段式新闻报道的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战争。另外,在甲午战争过程中,因为许多士兵来自贫苦人家,他们要写信报平安,连寄信回去的条件都没有,一些地方性的小报就免费刊登家书作为稿源,非常受欢迎。从那时开始,一些主要大报的汉字也开始增加注音,也就是说,这时以汉字为主的精英读写圈开始发生了沉降。简而言之,这个下沉首先是脱离经典,其次是注音化,再次是加上配图。大报则还要改变报道形式,在俯视性的精英评论之外,增加平视性的前线实时报道。日本处在这样一个急剧的变动之中,中国也一样,《申报》《点石斋画报》的报道都是非常直观亲民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甲午战争作为第一场东亚近代大战,它搅动了汉字圈的日常,又逐渐变成了另一种新的日常。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精英共同知识空间往下沉的过程。我在书中还讨论过,从太平天国运动到甲午战争期间,对死去的人的祭祀权也在下降、沉降。这个趋势在东亚非常明显。
战争搅动了社会,从知识史的角度来讲,知识空间重组了,在重新缔结。原来的秩序,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秩序,文本的秩序——比如经史子集之间的关系、正文与脚注的关系、汉字与和文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近代东亚知识空间再缔结的一些因素,能更具体地谈谈吗?
孙青:知识空间是有社会性的,是一个共同体。我们现在痛感于信息茧房,就是面对同样一个文本,大家的知识准备不一样,就会鸡同鸭讲。语言不通多少可以通过翻译解决,但是没有共同的知识结构就无法交流。
近代东亚的知识空间重新缔结,是跨越语言、跨越阶层的,是有抓手的。它有一个具体的聚合方式,围绕哪个议题展开、变成一个怎样的群体,都是明确的。比如说我们围绕甲午战争,围绕着文明决定论,围绕某一个文本,就变成了一个共同群体。近代东亚的汉籍,使用得越广泛就越有讨论价值,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共同文本。懂汉字的朝鲜人、越南人和中国人都在使用,而且大家都围绕这个文本进行讨论、批注,这时这个文本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公共议题。比如,书中提到的围绕《中东战纪本末》的日译本形成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在一个讨论圈里,就像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能够讨论很多问题。这就是我尝试描述的知识空间,它有物理性的空间,也有社会性空间。我想重点讨论的是社会性空间,这个空间如何缔结,这是这本书想要表达的。
技术变革和城市化导致的文化版图变化,以及传播技术的发展,包括西方记者的报道,实际上都在扩展这个知识空间。而且它还有很重要的传播功能。一种是横向传播,一种是纵向传播。横向传播是空间的、区域的。纵向传播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历时性的,如何流传,还有一个是人群的,就是跨越阶层的纵向传播。甲午战争时期就发生了很多跨越阶层的传播。跨越阶层的传播很难,有几个条件。比如我以前也讨论过白话读写的问题,读写普及不光要提高识字率,更要解释读写的规则,比如要知道书是从右读到左,如何标注,还要明白写作者与读者间的修辞默契(如使用“敝帚自珍”等谦辞并不是真的在讨论扫帚)、为什么书需要有序言,要明白这些东西,光识字是不够的,是无法跨越阶层传播的。
甲午战争加速了这个过程。客观上因为当时存在一些机制,例如前面提到的日本的报刊媒体的机制变化,另外主观上,文明决定论带来的文明改造,是战后东亚很多地区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启民智、扩大政治参与等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战争要求的动员力度比日常动员大得多,日本必须把全民动员起来,中国也进入了军事动员时代,所以当然是加速的。
再说文化版图的变化。过去文化中心和行政中心是重合的,基本上省道府县,只要涉及科考,往往是区域文化中心。但是甲午战争前后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口岸城市,比如上海,制度性媒体开始出现了。另外是废科举兴学堂使读书人逐渐向大型城市聚集,造成了文化中心与基层考场的剥离。战争确实会加速文化版图的变化,但文化版图的变迁并不仅仅是因为战争。它关涉很多其他因素,如文教改制和交通因素等等。
这种再缔结还源于标准化战争技术的全球传播。近代战争同时也是一种技术和知识环流。江南制造局有很多外国专家,甲午战争实际上往往是外国人跟外国人打——中方有很多洋员在船上,外交谈判也有很多洋人参与。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生产厂商也参与其中。军备供应将坚船利炮引入战场,成为近代战争的重要方式。为了应战,就要迅速造炮台、买船舰,再从引入供应方技术人员到培养本土人才等等。同时,近代国际战争的规则,诸如如何宣战、如何界定战争结束,这些在前近代是不确定的,要到甲午战争时代才相对明确。
在引入近代军事技术、规则和训练军事人才时,便涉及了如何书写战争专史。这套机制是德国人在建立现代军事院校时就确定的,与我们史学传统中原有的体例并不相同。德国的战史课程在十九世纪初传到荷兰皇家海军学院等军事院校,又传到日本,再为中国精英所知晓。德国的军事训练里必须要有战史,他们是通过战史来学习战例的。当传到日本时,由于当时保守的陆军部不允许对师级以上军事决策做评价,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战史的这一功能。而中国人在接触到这一套系统时,则开始探讨如何提升兵学在中国的地位。传统的兵学只有城防战术,没有具体的历史案例。即使讲到淝水之战这样以少胜多的战例,也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深入具体过程。因为传统上并不认为打仗需要从具体战史中学习,纸上谈兵是可笑的。另一方面兵学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史学无需承担解决这类问题的任务。但是这种“知识秩序”到了晚清开始出现变化,魏源就提出,应该从历史战例中吸取经验。有意思的是,魏源的《圣武纪》先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翻译到日本去的,有十几个版本,六十年代结合了兰学的内容,某些观点和语词又再以“兵学”的形式回传中国——这就是“环流”的一个例子。
标准化的知识还有很多,比如电报等通讯技术、现代标准化时间、空间测量等等。整个二十世纪实际上是战争推动发展的时代。
说到知识的流动,您为什么用“环流”而不是一般常用的“流动”或“互动”,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孙青:互动是点对点,环流是多向多点流动。“环流”是张伯伟教授提出来的概念分析工具,它未必是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单向流动,而可能是在两地或者多地之间多向、多次发生的流动。“环流”是没有单一线性秩序的,有时恰恰打破了固有的秩序。其展开模式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这也可以认为是战争搅动“日常”的一个后果。
比如姚锡光在日记中记载了每日和自强学堂的学生王松臣一起译“英国人所著甲午战史《中东战记》,至二更回家”的情况,记录非常多。《中东战纪本末》不是汉文写的吗,那他是在“译”什么呢?后来有学者张黎源考证,当时有一份在天津出版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刊登过北洋水师德国炮术教习瑞乃尔(Theodore H. Schnell)为德国政府撰写的两份报告的英译。其中一份德文报告底本是一篇按时间顺序描述军事事件的《威海卫之战》(Der Kampf um Wei-hai-wei),先发表于《科隆公报》(Cologne Gazette),后被英译刊载。而姚锡光曾称读到王松臣从英人译入的“洋员瑞乃尔辩词……言失刘公岛事”,感到“怒眦欲裂”。则当时他们为编纂《东方兵事记略》,每日在“译”的应该就是这个文本。《中东战纪本末》中文本他有,是托了叶瀚到上海买来寄给他的。这就是环流。姚锡光作为一个当事人曾参与甲午战争,但他的信息还要靠英文报纸来补充记忆,因为当事人只能看到局部。他让人搜集《中东战记本末》,并翻译英文版,还要找人做口述,然后才开始写作。他对《中东战纪本末》的事务化记录方式不满意,因为这样会使得战争责任者不明确。
书中第七章还涉及几个有趣的例子。比如日本军官成泽茂马战后向日本原驻法公使曾祢荒助学习法语,曾祢泽将法国步兵大尉索瓦(Maxime Joseph Marie Sauvage)于1897年在巴黎出版的自著甲午战史La guerre Sino-Japonaise 1894-1895 (《中日战争,1894-1895》)推荐给成泽作为阅读材料,成泽随后又把这本书翻译成了日语。实际上,在索瓦战史所列的参考书中,又有之前有贺长雄以法语出版的《甲午战争国际法》。又比如,日本当时有名的新闻记者藤野房次郎用日语翻译了林乐知、蔡尔康的《中东战纪本末》。此书是战后广学会分赠给大山岩和山县有朋的,一位武官获知后推荐给了藤野。而藤野又在通达汉语公文的宫岛大八(曾师从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三岛广(三岛毅之子)等人的帮助下将其翻译为日语。很明显,对战事的叙述、翻译与讨论,是发生在一些特定人群之间的。这些人群通过这类活动形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拥有一些共同文本,如有贺长雄《甲午战争国际法》、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等;还形成了一些共同知识,如汉字书面语、法文、汉字公文书的读解和翻译,以及对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术语、制度与人事的共识性理解等等。
这便是本书所要观察和描述的社会性知识空间,本书实际上就是想要去追问,近代国际战争、全球化等十九世纪中后期发生的全局性变动,如何搅动了旧有的知识秩序和知识空间,又缔结了何种新的图景?实际上,成泽茂马和藤野房次郎的日译本,又变成了甲午战后某种新的“共同文本”,只是它们的读写圈可能扩大了或者发生变动了。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